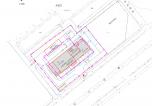新榮區(qū)晨景展無(wú)窮魅力
在通往大同市新榮區(qū)拒墻堡宣寧城遺址的路上,秋季的原野展現(xiàn)出成熟的美麗,厚重而又凝煉,繽紛而內(nèi)斂。在當(dāng)?shù)乩先说闹更c(diǎn)下,我們佇立在南堂寺碑下搜尋一個(gè)千年未醒的夢(mèng),而那僅存的碑文字跡經(jīng)過(guò)風(fēng)雨的侵蝕已變得漶漫不清。一個(gè)字能夠露出一半真容已經(jīng)是蒼天對(duì)我們的恩賜了。展露在我們面前的碑文仿佛是一部天書(shū)在等著我們?nèi)テ谱g和解讀。墨和宣紙已無(wú)法給我們作出一個(gè)正確的解釋。無(wú)奈之下,我們只好費(fèi)力地摸索、猜測(cè),連接字與字、句與句的內(nèi)在文意,思忖和辯別。每猜出一個(gè)字我們都會(huì)欣喜若狂,而沉默的巨碑顯得漸漸沉不住氣了,秋風(fēng)也狂燥不已。太陽(yáng)已漸漸西移,在費(fèi)了整整半天的時(shí)間后,一個(gè)秘密,關(guān)于南堂的秘密清晰地呈現(xiàn)在我們面前。
時(shí)間能夠改變一切,繁華錦繡總有一天也會(huì)湮沒(méi)在歷史的塵埃里。滄海桑田、玉兔東升、金鴉西墜,生命的河流訴說(shuō)著輪回的美麗。歷史與人生總會(huì)像棋局一樣變幻莫測(cè)。“青山依舊在,幾度夕陽(yáng)紅”。婉約的愁?lèi)潟r(shí)時(shí)撥動(dòng)著人們靈魂深處那個(gè)懷舊的結(jié)。
往事如煙,歷史的真實(shí)瞬間便得到還原。南堂寺,圣境清音,梵唄綿延,一個(gè)神仙般的境界漸漸拼接了起來(lái)。遼時(shí)創(chuàng)建,光緒二十九年重新修建的南堂寺,在此后的歲月里,便又像流星一樣隕落了。如今人們?cè)谙氯A嚴(yán)寺的山門(mén)內(nèi)還能見(jiàn)到當(dāng)年南堂寺造型古樸、端莊典雅的鐵佛,圓通寺藏金閣內(nèi)也有原南堂寺的大勢(shì)至菩薩。它們見(jiàn)證了此消彼長(zhǎng)的塵世變遷,但它們依舊默照著大地上生生不息的蕓蕓眾生,仿佛在訴說(shuō)著什么,仿佛什么也沒(méi)有說(shuō)。元代劉秉忠這位絕代奇僧,就是在南堂寺告別了能海法師,跨出山門(mén)輔佐元帝東征西討,換來(lái)了一個(gè)完整的天下。
一條蜿蜒曲折的古道延伸向遠(yuǎn)方,遠(yuǎn)方有黑色的樹(shù)木和一條光潔的河流。古城墻像個(gè)疲憊蒼涼的武士寂寞地躺在大地母親的懷里,舒展開(kāi)兩條長(zhǎng)長(zhǎng)的臂膀,呼吸著塞上自由自在的空氣。仿佛一切都沉寂下來(lái),靜得沒(méi)有一絲聲音。整個(gè)歷史仿佛就在一個(gè)人的意念中完成,展現(xiàn)著一幅幅立體而又靈動(dòng)的畫(huà)卷。忽爾時(shí)光倒流,人們穿梭在清明上河圖的幻覺(jué)里,忽爾千年后的空間又紛至沓來(lái)。而此刻,在你的腳下厚重而蒼涼的土地承載著逝去的刀光劍影,也承接著文明薪火的傳遞。通向大漠的和平使節(jié)在出關(guān)后深情地回眸,讓人黯然傷神;取經(jīng)僧侶在經(jīng)過(guò)你身邊的一剎那,讓陣云密布的天空頓時(shí)露出了祥和的光茫;而大漠潮水般涌來(lái)的刀矢人潮就在厚重的黃土層里翻涌著紛亂的鐵蹄和如雨的箭簇。血與劍,商人與行旅,離亂和團(tuán)聚,戰(zhàn)爭(zhēng)與和平……所有的一切都濃縮在這方已逝去的古城。
離開(kāi)南堂寺往西走,在荒涼的古堡南邊不遠(yuǎn)處的曠野里,驀然出現(xiàn)了一尊突兀的塔,幽幽地發(fā)出一種冷艷的光芒,玄鐵樣的質(zhì)感,卻顯靈動(dòng)與飛揚(yáng)。我輕撫著這座造型奇特頗具生命質(zhì)感的石塔,內(nèi)心里仿佛與遠(yuǎn)古進(jìn)行著一場(chǎng)對(duì)話(huà)。它有五米多高需三人伸開(kāi)雙臂才能合抱。塔剎如疊傘,塔基的上方有雙層蓮花瓣構(gòu)成的精美圖案。石經(jīng)幢上所記的經(jīng)文大都已無(wú)法辯認(rèn),但依稀還能讀出這樣幾行大字:大金西京宣寧曇開(kāi)佑寺故都僧錄侍菩薩戒成慧大師……金大定十六年清河張寔書(shū)。我們此行也許是拜謁成慧法師塔的最后一批游客,此后不久,成慧法師塔便在楊州窯的原野上消失了,化作一片朦朧的記憶。